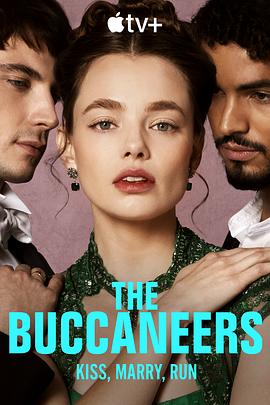剧情介绍
好一会儿,才听顾倾尔自言自语一般地开口道:我一直想在这墙上画一幅画,可是画什么呢?
听到这句话,顾倾尔安静地跟傅城予对视了许久,才终于低笑了一声,道:你还真相信啊。
这种内疚让我无所适从,我觉得我罪大恶极,我觉得应该要尽我所能去弥补她。
我好像总是在犯错,总是在做出错误的决定,总是在让你承受伤害。
一直到那天晚上,她穿上了那件墨绿色的旗袍
那个时候我有多糊涂呢?我糊涂到以为,这种无力弥补的遗憾和内疚,是因为我心里还有她
现在是凌晨四点,我彻夜不眠,思绪或许混乱,只能想到什么写什么。
去了一趟卫生间后,顾倾尔才又走进堂屋,正要给猫猫准备食物,却忽然看见正中的方桌上,正端放着一封信。
他们会聊起许多从前没有聊过的话题,像是他们这场有些荒谬有些可笑的契约婚姻,像是她将来的计划与打算。
喜欢看【你好神枪手电视剧免费观看啊】的人也喜欢
美剧• 热播榜
- 1第10集完结萤火虫之墓
- 2第6集完结神雕侠侣2014
- 3第7集完结韩剧她很漂亮
- 4第8集在线动漫观看
- 5第18集信号韩剧
- 6第6集完结电视剧大清风云
- 7第7集完结饕餮记40集全免费观看高清
- 8第03集完结500篇艳妇短篇合换爱视频
- 9第16集完整版电影
- 10第8集《我唾弃你的坟墓》